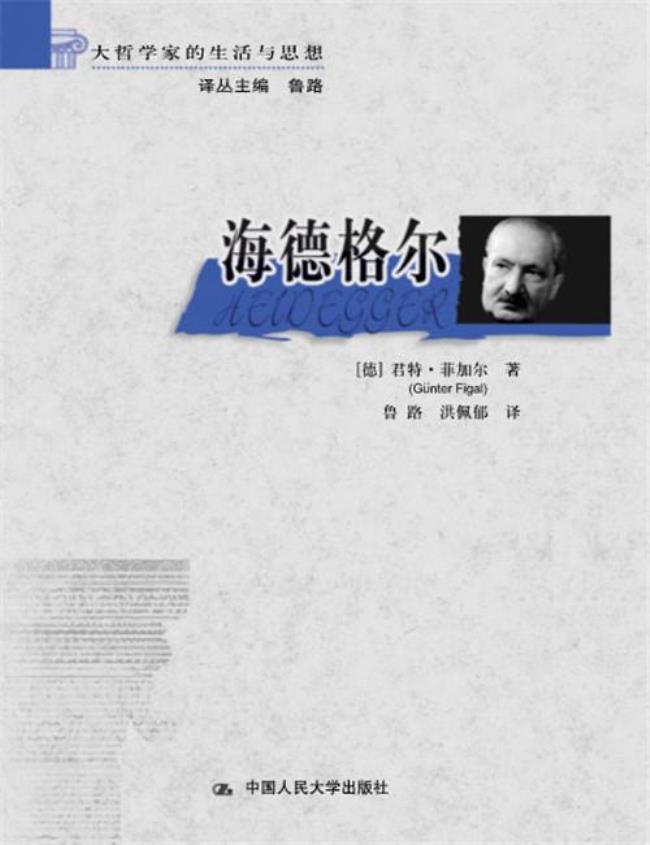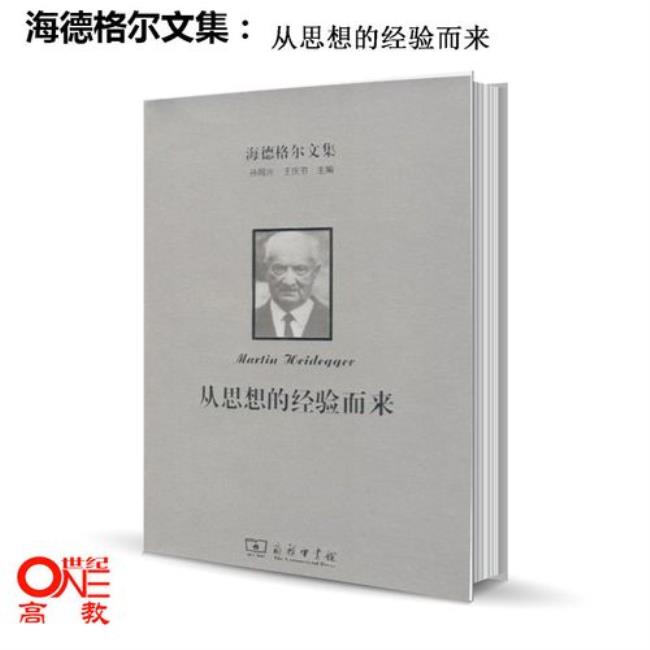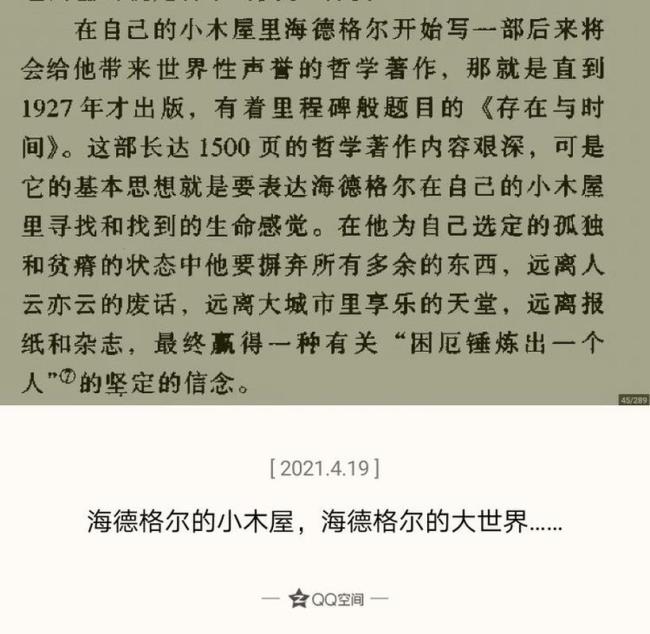依据海德格尔的见解,“本质”应被解作动词性的“本质现身”,意谓“在场着”和“不在场着”的“本质现身”。本质现身并不是作为超感性的永恒领域,而是有所遮蔽的在场状态,是一种闪光的纯粹性。语言在其自身的抑制中,拒绝向我们通常的观念全盘托出它的本质。难以捉摸的“本质”,并不是外在于我们,也不是通过概念与论证等手段追求来的,而是在其在场和持续之际关涉着我们。或者说,我们总是已经逗留于与我们亲密相关的本质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才能够有关于语言的经验,尽管我们尚未从这一经验中获得洞见。但这正是尚未被思并有待被思的东西。因为语言经验带来的并不是昭然若揭的明朗,而是自行隐蔽着的暗冥。显然,我们关于语言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从追问“根据”中产生的,而恰恰是由于我们已经在语言上取得了一些经验,语言之本质总已经关乎着我们生存的可能性。在这时,人不得不收起自身作为说话者的“主体性”,让位于“语言说话”的来袭,并应合于语言之纯粹所说。对此,海德格尔提出一个猜度:“语言之本质就在道说中。”
在由根据向本质的本真性回归下,思想的姿态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因此,要回归到思想更为本真的姿态,需要先放下对本质的追问和对根据的寻求,转向这样一条道路,即对“一切追问所及的东西的允诺的倾听”。这里不难理出海德格尔在思想道路上的转变,即从追问的道路跨越到倾听的道路。所谓“倾听”,并不是去倾听我们已经熟悉和理解的东西,而是在言说的困境中,接受和顺从语言之要求,尝试着留心语言未被说出的东西以及我们与语言的本质之间关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