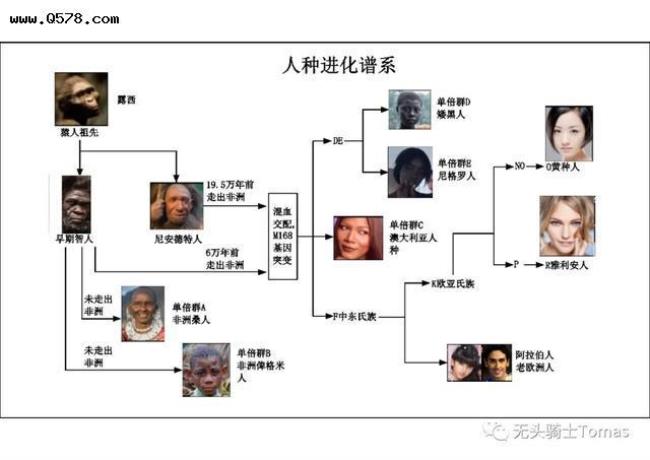这就要谈及北美最常见的一个梗:美国和加拿大人对“别人家的医疗制度”和“别人家的福利制度”的羡慕。
美国人经常会羡慕加拿大的全民福利医疗,在离加拿大近在咫尺的华盛顿州,许多美国人会对来这里“蹭油”(美国油价比加拿大便宜得多,很多住在大温哥华地区的加拿大人周末会带着油桶过境加油)的加拿大人称羡不已,说“你们换个肾都不要什么钱,我们发个烧就脱层皮”,因为两国都进入老年社会,而老年人慢性病特别多,加拿大的福利医疗对老年人这种没事就要看病、但说不清到底要看什么病的状况十分友好,因此不少美国人一到退休就想方设法移民到加拿大去“蹭福利”。
但加拿大人却常常羡慕美国的医疗:效率高,设备好,只要舍得花钱,就能又快又好地完成急救,而不会像在加拿大那样,要从家庭医生到专科医生,再从专科医生到医院那样一层层排队(手术平均轮候时间长达几十天,我去年一个急性阑尾手术就等了一整天,还是因为被误诊为肺炎、医院惟恐传染疫情才特别加快,一个熟人同期同类手术等了7天没做上),事实上加拿大这边出了重大车祸之类需要大规模急救时,经常要动用直升机把人往美国送,因为留在加拿大排队弄不好没上手术台先进太平间了)。
当然相反的例子也有——比如加拿大主张“一大二公”的工团党派新民主党就经常指责主张自由经济的保守党人“羡慕美国医疗”,而反对全民医保的共和党人把最执着主张全民医保的民主党最资深众议员佩洛西调侃为“加拿大人”已经很多年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围绕福利医疗和整个福利体系的“围城效应”
在福利国家里,人们更多体会到的是福利体制的缺点。
在政府看来,福利体制造成政府开支浩繁,财政压力巨大。
退休金方面,法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因为退休金开支庞大,法国年赤字高达GDP的7.5%,远高于欧盟3%的上限,每年养老金开支高达320亿欧元,且由于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2050年将升至1140亿美元;英国到2050年退休金领取者人数将上升50%;而希腊则更成为被退休金压垮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平均退休年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只有令人惊讶的53岁。
医疗方面问题更突出。如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导致医疗开支庞大、效率低下。加拿大近年来医疗保健年支出都在1500亿加元左右,人均约4000加元,居世界第五位,但如此庞大的开支却得不到应有的效率,全国仅3000多万人口,竟有500万人口没有家庭医生,近100万人口在等待治疗,许多医院设备陈旧落后。不仅如此,福利医疗体系导致病人等候时间长,据加拿大“候医联盟”在全国1189个专科医生处所作的调查,病人等待手术的时间平均要18周,且在所统计的21种病症中,等候时间超过18周的竟有15种之多,因等候时间过长导致病情耽搁甚至死亡的医疗纠纷官司,在加拿大见怪不怪,每年因看病排队所造成的损失就达15亿加元以上。
高税收、高福利更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在希腊,过高的税收导致企业效率低下,而高福利则让员工不思进取;在德国,为维持高福利而实行的高税收,导致大量富人移居海外,许多企业也宁愿“移民”,造成产业和财富的流失;在北欧,由于福利制度给不工作者的福利甚至超过许多普通工薪阶层,导致许多人宁可流浪也不工作,一些企业因员工不怕丢饭碗,缺勤率、请假率常年维持在20%左右,致使生产效益长期低迷;高福利制度不仅让不少福利国家债台高筑,还人为抬高了劳动力成本,造成国家竞争力的下降。
正因如此,福利国家才一度兴起“向美国看齐”的潮流,希望通过“美国式”的“去福利化”,给政府开支“瘦身”,从而提高社会活力和竞争力,减轻社会负担。而在这些国家民间,因高福利所带来的前述弊端令他们感同身受,在对前景保持乐观的情况下,人们也普遍愿意少享受一点福利,以换取更少的税额,更多的收入,和更优质的社会服务。
而在美国则正好相反。
在美国,宁可低福利也要低税收,宁可缺少公平也不可缺少效率的“美国梦”共识,只有在在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美国人收入预期高企、消费欲望高涨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因为惟有财富滚滚、机会无限,普通美国人才会把效率和机遇放在第一位,而相对忽视医保的全民性和公平性——反正也不是没钱给商业医保买单。而持续高企的失业率,使许多失业者游离于商业医保之外,因为再没有公司为他们买单;衰落的经济,让普通美国家庭的未来收入预期大跌,大手大脚透支花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一切对于中上层美国人而言,或许触动不大,但对于广大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则影响巨大,俗话说得好,饱暖思富贵,饥寒思温饱,此时此刻,更多普通人渴望一个全民性、福利性的医保体系,以覆盖越来越多买不起商业医疗保险、更看不起自费病的美国家庭,也就不足为奇了。